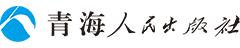轗轲者点燃膏火照亮的博大诗境(六)
2020-07-27《高车——昌耀诗歌图典》原文地址
轗轲者点燃膏火照亮的博大诗境(六)
文/马钧
1957年,昌耀写了一首仅有8行的短诗《高车》。1984年年末,昌耀对这首27年前的旧作作了删定,并加了一个题记(他自己称为“序”):“是什么在天地河汉之间鼓动如翼手?……是高车。是青海的高车。我看重它们。但我之难于忘情它们,更在于它们本是英雄。而英雄是不可被遗忘的。”其中诗人创造了“翼手”这么一个陌生的词语。在汉语语汇的构成里,以手作为后缀组成的词语,比如“舵手”“水手”“旗手”“歌手”“棋手”等,都是指所从事的职业或者动作。那么“翼手”又是什么意思呢?除了“翅膀”这个“翼”字的常见义项,还有旧时军队编制分左、中、右三军,左、右两军叫作左、右翼。还有一个偏僻的义项,是“十翼泛清波”里当“舟”用的这个意思。这几个意思,都没法与此诗的语境吻合。参照诗人其他的诗篇,我发现昌耀喜欢拿车轮这个带着运动感、速度感的词语,和“翼”字搭配在一起,比如《木轮车队行进着》:“——这车队/一扇扇高耸的车翼好像并未行进着?/这高耸的一扇扇车翼/好像只是坐立在黄河岸头的一扇扇戽水的圆盘?”“木轮车队高耸的轮翼始终在行进着。”比如《雄风》:“我深信/只有在此无涯浩荡方得舒展我爱情宏廓的轮翼。”比如《河床》:“我爱听兀鹰长唳。他有少年的声带。他的目光有少女的/媚眼。他的翼轮双展之舞可让血流沸腾。”比如《感受白羊时的一刻》:“天路纵驰。翼轮阑干。梦影华滋”;比如《骷髅头串珠项链》:“……插立在车翼的白布经幡像竖起的一只大鸟翎毛满是尘垢。”如此看来,“翼手”是昌耀的一个拟人化了的曲喻,暗含有飞驰的运动感,有若屈原“乘回风兮载云旗”里那般车轮的速度与激情,是一种驱动运动的力量,一种充盈的生命力,一种如他所欣赏的“瞬刻可被动员起来的强大而健美的社会力量的运作力”,一种恢宏、盛大、厚重、庄严的演奏——“是以几百、上千个体力劳动者同时运作爆发而得的体力作为动力,带动特殊器械装置为之鼓风,使气流频频注入数百根、数千根金属或木质管孔,发出来足以与其规模相称的、令人心旌摇动的乐音。”总之,“翼手”是一种澎湃激情和生命强力的象征,是他的大诗歌观在审美表现层面的最初呈现。
现在,我们回到《高车》的前两节 :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昌耀锁定西北大地以往常见的那种大轱辘车来书写,但对其形状之大并未作特写处理,而是将其置入一个大视角、超长焦、大纵深的空间,并且不是将高车当作静物来描写,而是作为持续移动的意象来处理。让人们费解的是,在大地上驰行的高车,怎么会跑到天上“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呢?须知这不是诗人的幻想或产生的幻象,它是昌耀对视觉经验里前景和后景相重叠后所形成的视觉错觉的巧妙的诗性转化,是昌耀对青藏高原极高的空气透明度下清晰星象的敏锐洞察。这种视觉错觉,一直被摄影家、画家、电影摄影师们屡试不爽地运用于奇妙画面的设计。擅长绘画的作家阿城在《孩子王》里借王福的作文,就利用这一视觉错觉写出与昌耀诗句异曲同工的画面:“早上出的白太阳,父亲在山上走,走进白太阳里去。”后来昌耀写下的“一百头雄牛低悬的睾丸阴囊投影大地。/一百头雄牛低悬的睾丸阴囊垂布天宇”,同样采用的是宏廓的视角,但这一次垂布天宇的睾丸阴囊已不是诗人的视觉错觉,而是诗人夸张性的主观想象。
利用天地之间形成的夹角来成像造境,是昌耀书写宏大境界的视觉和心理的双重经验。偏于视觉的,像《去格尔木之路》里这样的描述:“盐湖已被挤压于天地之夹层。”(利用空间中物体大小的反衬效果)偏于心理的,像《巨灵》里这样的描述:“我攀登愈高,发觉中途岛离我愈近。/视平线远了,而近海已毕现于陆棚。/宇宙之辉煌恒有与我共振的频率。/能不感受到那一大摇撼?”
用天象作为诗歌意象,也是昌耀诗歌营造恢宏、崇高意境的重要途径。其本质涉及昌耀诗学中极为醒目的一个特点:广阔、深邃的时空观。王国维先生当年在《人间词话》列举“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澄江净如练”“山气日夕佳”“落日照大旗”“中天悬明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古典诗词片段,批识到 :“此等境界,可谓千古壮语。求之于词,则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静安先生没有明确点出边塞或者游牧民族生活的疆域,往往因为辽远开阔的地理环境会给人们视觉经验上带来一望无际的视觉感受。这种视觉感受随后又会赋予人们心理感受上的博大与崇高。纳兰词境的高旷,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唐代边塞诗人开启的博大诗境在清代迢递的余绪,昌耀则是在当代新诗里一次更其遥远的接续和转型。
学者王锺陵在《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研究》中专门论及“唐人的时空观”——“唐人的边塞诗,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三个因素的结合:阔大的地域感,对边地季候景物的描写,以及征人的或豪迈、或悲切的种种心理之表现。”“唐人所感受的这样一种阔大空间,不再仅是平面的展开,它是立体的、多维的,并和时间因素紧紧交织着,它也不再仅用之以表达一种气势了,它内蕴着丰富多样的内容,有着特定的景观和人物的情思。外延的开阔和内蕴的丰富,形成了壮阔而又情味深长的亦即可用‘壮美’一词加以概括的意境。”
《高车》一诗不是昌耀重量级的作品,但它显露出昌耀诗学的一个重要审美取向——宏大的时空观,把物象或事物放置到天地河汉之间这样一种广大而实在的空间里来打量。这已不再是唐代以前或者《楚辞》里那种通过神话思维、幻想创造出的宇宙空间,而是唐代边塞诗人们普遍的视觉经验和心理气象。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审视,昌耀的咏青诗作,既是对边塞诗诗脉的遥远呼应,更是对边塞诗不可同日而语的一次全新编程、全新掘进,将昔日政治化、社会化的诗歌维度代之以审美化、地域化的诗歌维度。
具体来说,时空世界在昌耀这里再度被广化。《在雨季:从黄昏到黎明》里,昌耀借用夕阳的视角,含纳了长河上下游这么一个超然的共时性视域空间:“雷雨之后,夕阳/品茗长河上游骤然明亮的源头,/见下游出海口一只无人的渡船/悄悄滑向瓦蓝。”1962年写下的《断章》,是昌耀早期博大风格的代表,那种磅礴的气势和宇宙感,完全是被惠特曼《自己之歌》《大路之歌》式的整体诗学所唤醒和激活的一种抒写 :“这样寒冷的夜……/但即使在这样寒冷的夜/我仍旧感觉到我所景仰的这座岩石,/这岩石上锥立的我正随山河大地作圆形运动,/投向浩渺宇宙。/感觉到日光就在前面蒸腾。”昌耀的这种超然的共时性视域空间,已经成为他稳定的心理结构和审美反射习惯,所以即便到了迟暮风格时期,他仍旧在延续古代诗人未能抵达和书写的超然的共时性视域空间——《莞尔——呈献东阳生氏》:“穿过田野,朗极的黎明,银月照我西山,旭日徂彼东岗,在清风徐徐的节律我已面北同时朝觐两大明星体,而怀有了对于无限的渴念。”
需要进一步强调,昌耀在其迟暮风格时期,他早期的惠特曼式的抒情,便更多地转向鲁迅《野草》式的抒情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化的风格,尤其是他具有明显陀氏思维倾向的多重体验,激活了他对同时共存的事物的特别关注与兴趣。比照陀氏艺术感知世界的特点,我们在昌耀的诗里发现他也像陀氏一样,把“一切分离开来的遥远的东西,都须聚集到一个空间和时间‘点’上”,“只有经过思考能纳入同一个时刻的东西,能在同一时刻相互发生联系的东西”,才能成为他表现的题材。这一具有狂欢体特色的时空观,特别擅长于采用宇宙度量来创作具有宇宙时空广度和深邃度的形象和情景,是作家和诗人具有宇宙意识的审美观照。(参照小说《围城》里的如下表述:“天空早起了黑云,漏出疏疏几颗星,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白天的汪洋大海,这时候全消化在更广大的昏夜里。衬了这背景,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只心里一团明天的希望,还未落入渺茫,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一点萤火似的自照着。”)
在同一时间呈示与叠加不同事物,这在中国的古典诗歌里已有体现,如鲍照的“居人掩闺卧,行人夜中饭”,高九万的“日暮狐狸眠坟上,夜归儿女笑灯前”。古典诗歌限于格律与对仗,一般只能将两件事情并置于同一时间。昌耀却能做到将三件事情并置于同一时刻。像《旷原之野——西疆描述》:“晚照中的卧牛正以一轮弯弯的犄角/装饰于雪山之麓。靓女的/乔其纱筒裙行行止止……/花灯般凝止。/绿洲匍匐的晚祷者以沙土净沐周身——”;像《薄曙:沉重之后的轻松》:“薄曙之来予我三重意境:/步行者橐橐迫近的步履。/苇荡一轮惊鸟戛然横空。/漫不经心几响犬吠远如疏星寥落。”
正像我们前面引证学者针对唐朝诗人时空观时所阐述的一种观点,唐人时空观不再仅是平面的展开,而是立体的、多维的,并和时间因素紧紧交织在一起。同样,在昌耀博大的空间感里,经常会注入时间上的邃远感,这是昌耀时空观所发展出的一种诗歌类型。比如,《船,或工程脚手架》:“水手的身条/悠远/如在/邃古”;《寄语三章》:“披着粼光瑞气/浩浩漭漭轰轰烈烈铺天盖地朝我腾飞而来者/是古之大河。”;《激流》:“沿着黄河我听见跫跫足音,/感觉在我生命的深层早注有一滴黄河的精血”;《群山》:“这高原的群山莫不是被石化了的太古庞然巨兽?”
昌耀的这种邃远感大半基于久远的历史或者漫长的时间,这也是古典诗歌里惯有的思维和技法。可是昌耀比他的前代诗人们走得更加辽远,后来居上。当他从生物学和生命科学来拓展他的邃远感的时候,他便跨入了现代诗歌的语境,跨入了前人从未书写过的崭新语境;这也是与他前后出道的诗歌同行未必能及的地方。《与梅卓小姐一同释读<幸运神远离>》:“人间从来就是现世生者的‘涤罪所’,苦难中的形骸思虑营营,历历可见:人满为患,金钱肆虐,半个世纪,尤以现今为最。厄运之不可摆脱犹如存在于细胞核染色体的遗传基因,一个新的生命一旦完成,厄运已潜在其中。人虽不能透过时空预见每一细节,但细节迟早会一一应时而显现。一个后代子孙的命运,甚至可以推其谱系溯源到其远代母亲——尚在母体胚胎发育中的——卵巢的一粒卵子。这种邃远感,有如从相对的两面互为反射、互为复制、互为因果的镜子中所见无穷深远的物象。
河 床
(《青藏高原的形体》之一 )
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
白头的雪豹默默卧在鹰的城堡,目送我走向远方。
但我更是值得骄傲的一个。
我老远就听到了唐古特人的那些马车。
我轻轻地笑着,并不出声。
我让那些早早上路的马车,沿着我的堤坡,鱼贯而行。
那些马车响着刮木,像奏着迎神的喇叭,登上了我的胸脯。
轮子跳动在我鼓囊囊的肌块。
那些裹着冬装的唐古特车夫也伴着他们的辕马谨小慎微
地举步,随时准备拽紧握在他们手心的刹绳。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倒的河床。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
是的,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我是滋润的河床。我
是枯干的河床。我是浩荡的河床。
我的令名如雷贯耳。
我坚实宽厚、壮阔。我是发育完备的雄性美。
我创造。我须臾不停地
向东方大海排泄我那不竭的精力。
我刺肤文身,让精心显示的那些图形可被仰观而不可近狎。
我喜欢向霜风透露我体魄之多毛。
我让万山洞开,好叫钟情的众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
我是父亲。
我爱听兀鹰长唳。他有少年的声带。他的目光有少女的
媚眼。他的翼轮双展之舞可让血流沸腾。
我称誉在我隘口的深雪潜伏达旦的那个猎人。
也同等地欣赏那头三条腿的母狼。她在长夏的每一次黄
昏都要从我的阴影跛向天边的彤云。
也永远怀念你们——消逝了的黄河象。
我在每一个瞬间都同时看到你们。
我在每一个瞬间都表现为大千众相。
我是屈曲的峰峦。是下陷的断层。是切开的地峡。
是眩晕的飓风。
是纵的河床。是横的河床。是总谱的主旋律。
我一身织锦,一身珠宝,一身黄金。
我张弛如弓。我拓荒千里。
我是时间,是古迹。是宇宙洪荒的一片腭骨化石。是始皇帝。
我是排列成阵的帆樯。是广场。是通都大邑。是展开的
景观。是不可测度的深渊。
是结构力,是驰道。是不可克的球门。
我把龙的形象重新推上世界的前台。
而现在我仍转向你们白头的巴颜喀拉。
你们的马车已满载昆山之玉,走向归程。
你们的麦种在农妇的胝掌准时地亮了。
你们的团栾月正从我的脐蒂升起。
我答应过你们,我说潮汛即刻到来,
而潮汛已经到来……
1984.3.22—4.20
作者简介:昌耀(1936—2000),当代著名诗人,被誉为“诗人中的诗人”。出版诗集有《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昌耀的诗》《昌耀诗文总集》等,长期生活于青海高原。
内容简介:本书围绕昌耀诗歌和生活,采用图、文、声并茂的形式编辑而成。主要收录昌耀书写青海和西部的近百首短诗,其中穿插上百幅与昌耀有关的手迹、书信、照片等珍贵资料。每首诗都录制成朗诵音频,置于每首诗歌前面,读者扫码即可聆听。另外,卷首还有著名评论家马钧撰写的万言长序,书后附有三万多字的昌耀年谱。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无疑为喜爱昌耀诗歌的读者提供了一场饕餮盛宴。
朗读者简介:吴旭威,青海省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资深记者、主持人(主持名旭东)。
王越,青海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青海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青海省“全民阅读”推广人。曾获中国新闻奖最高荣誉“长江韬奋奖”和全国“金话筒奖”等奖项。
程格,毕业于青海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青海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节目主持人。

热门排行